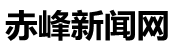本篇文章2401字,读完约6分钟
12月1日是世界卫生组织确认的“世界艾滋病日”。 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的迅速发展,更多的人敢于比较艾滋病歧视现象来发声。 但是,由于艾滋病的严重性及其传达方法,艾滋病依然陷入“污名”的困境,但这种“污名”经常向艾滋病感染者隐瞒自己的疾病,得不到正确及时的治疗,从而更大规模地扩张和感染。 艾滋病为什么被“污名化”得这么严重? 媒体医疗机构在其中起着什么作用? 社会变迁下的恐惧、误解和道德化污名是一系列社会文化相互作用的产物,与社会变迁密切相关。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首次出现hiv感染者病例,当时的舆论把艾滋病作为西方资本主义腐朽生活习惯的典型疾病,中国人也很快命名为“爱资病”。 早期,艾滋病污名也与社会身份污名相互作用,艾滋病风险一般与“外宾、回国者、边境居民、外国人”等他人形象有关。 改革开放给中国的社会思想带来了戏剧性的变化,对“舶来品”的恐惧和对新社会局面的激烈抵抗一起为艾滋病污名披上了合法性的外衣。 除此之外,20世纪80年代的人们对性有了新的看法,特别是年轻人从快感、亲密关系、个人自由等角度开始看到性。 20世纪90年代,为了防止非婚性行为激增、可能发生的性革命,政府将hiv定义为性传播疾病,深深引起了社会公众对hiv传播特定途径的想象。 性社会学研究者潘绥铭认为,艾滋病被视为千钧一发之际的整肃性道德工具,由此带来了大规模、与实际发病率相差甚远的另一种人工“恐惧症”。 到了世纪之交,“艾滋病高危人群”的污名聚焦于农民,发现卖血的中原农民感染了hiv病毒。 一项研究表明,公众正在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认知艾滋病毒感染者。 另一方面,感染hiv的吸毒者和商业服务人员的污名化起因于不良行为。 另一方面,通过卖血输血母婴传播途径感染hiv的人被认为是“无辜的受害者”。 但是,“无辜受害者”们的道德化并没有减少公众对艾滋病的恐惧和误解。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过度渲染间接被人们隔开距离集中看到,城乡流动之间的农民工被贴上了跨境新的标签,农村“艾滋病孤儿”成为另一个“特殊群体”。 除此之外,男性的行为往往形成与艾滋病相同的语言,男性的行为与感染艾滋病无异。 事实上,艾滋病最初报告的病例集中在同性恋群体,在其他途径发现感染的患者后,艾滋病与异性恋的相关性被打破。 一位学者说,艾滋病实际影响人们的公共化对主流人民构成威胁,引起了污名行为。 这是公众视野中艾滋病的污名与同性恋群体密切相关的原因之一。 随着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和媒体环境的开放,国民对同性恋群体的关心增加,总体上无法调和以前传达的舆论场和新兴群体舆论场,进一步扩大了恐惧和误解。 每年“艾滋病日”,志愿者都会上街要求拥抱,消除对艾滋病的恐惧。 大众媒体、医疗机构和公共政策的污名修辞在中国,大众媒体、医疗行业和公共政策的共同构建,造就了中国语境的艾滋病污名修辞。 中国的信息媒体从艾滋病发源地开始就备受关注。 1985年,中国发现第一位hiv感染者后,《人民日报》发表了20多篇关于艾滋病的报道,以艾滋病为“超级癌症”的名称。 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对艾滋病的科学认识,大众媒体对艾滋病的报道充斥着负面的叙事诗和猎奇的修辞,牵引了公众的恐慌心理。 媒体考虑到经济好处和传达战略,在很多报道中采用了“艾滋病村”、“艾滋病女性结婚”、“艾滋病杀手”等词语,将关于艾滋病患者的妖魔化形象设置在公众脑海中。 另外,在初期的艾滋病报道中,由于患者处于报道的边缘和失语状态,公众真正理解的机会不足。 通常,媒体有利于艾滋病知识的普及和传播,被认为是减少艾滋病污名的力量,但公众恐慌心理、政府权力的制约、医疗领域的用语与媒体多方向合流,媒体对艾滋病的去污匿名化变得困难。 在报道过程中,媒体大多依赖医务人员、医疗专家等强大的信息源,即使采用该用语也不能受到医疗界的影响,但在医疗机构和公共卫生行业中也存在对艾滋病的刻板印象。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隐喻》中指出,疾病作为社会动员和政治迫害的工具容易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 在说明hiv的原因和影响时,医学界将疾病和战争隐喻混合在一起,将艾滋病描述为“生命杀手”、“人体免疫系统和防御系统的侵犯者”等,敏感性高的人和hiv感染者为“目标群体”、“桥梁群体”、“高发区”等 火药气味的语言嵌入医疗用语,被各行业广泛使用,hiv感染者站在威胁公众的对立面。 除此之外,公共政策处理问题的行为习惯也加强了对艾滋病的污名。 在推进每年艾滋病防治的通知中,一定要把“高危群体”的定位和提高推广教育作为防治的主体部分,强调对这些群体的综合干预,把一部分群体放在道德低下的地方。 随着政策的消极解释,hiv感染者也面临着制度和法规的不平等。 国家最初发布的关于hiv暴露的法规---甘肃省卫生厅发布的《甘肃省艾滋病检查阳性结果告知规范(试行)》规定,在甘肃被查出hiv阳性的所有人必须在一个月内将自己的感染情况告知配偶或性伴,然后直到感染者的配偶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关于hiv身份暴露的强制规定完全无视感染者的心理感觉和精神状况,使感染者犯罪,使其想起社会心理学家链接和费伦指出的“结构性污名”,制度化的污名状况,如导致污名化者不利状况的政策和社会习惯 在大众媒体、医疗行业和公共政策的主导话语下,艾滋病的污名化变得比疾病本身更强烈的恐惧,经常带来困扰感染者、迷惑公众认识、社会隔离、资源分配倾斜等问题。 最可怕的结果可能是污名内化,即被污名化的人最终接受了关于他人的歧视行为和主流社会地位低下的观点。 【参考文献】1 .“污名和艾滋病的语言在中国”,张有春,《社会科学》,年第4期刊登。 2 .《疾病污名与身份污名的相互作用——以艾滋病污名为例》,高一飞,《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31卷第4期刊登。 (本文来自澎湃信息,越来越多的原始信息请下载“澎湃信息”APP )
标题:热门:“恐艾症”是怎么形成的?艾滋病的“污名化”之路
地址:http://www.cfcp-wto.org/cfzx/1804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