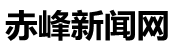本篇文章5872字,读完约15分钟
崇祯十六年( 1643年),日落西山的明帝国各方面都表现出大楼的衰退,除了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全面失败外,自然灾害和瘟疫也与这个泥足巨人纠缠在一起,难以支撑。 比起“晨病夕逝,全员战战兢兢,家族数十人,一夕业务员”的惨烈瘟疫,恐慌的杀伤力似乎更大,从11月开始堂堂正正的帝都北京城,竟然中午闹鬼了。 市井街头不断议论可疑的“鬼客”现象,位于繁华街道的店铺接待客人后,回头一看,收到的银两和铜钱变成了烧给死人的纸钱。 商店的房子要在商店门口放一个装满水的铜盆,让客人把钱放在盆里,根据是否声音和漂浮来区分银钱和冥币。 “白天鬼在市里,店家在有人收纸之前,分别倒水倒进门上,把钱扔进水里,辨别真伪。 “鬼行市上,啸语人间”的可疑情况崇祯皇帝也吓了一跳,命令龙虎山张应京真人做法事,结果没用。 "我做了酰基,毕竟没有经验. " 瘟疫引起的人心变化比瘟疫本身更可怕,帝国从上到下的手脚在心理上抛弃了人们。 “经济不景气,知识分子早卜有甲申之祸。 “战争、大灾害、大瘟疫几千年来,自然灾害、战争和瘟疫从未分家,彼此通过许多复杂的机制相互影响。 天灾饥荒扩大了老百姓的食谱,从观音土到他们能找到的野生动物,到与老鼠储存在地下的粮食同类的尸体,病情加剧的腺鼠疫和其他传染病在受灾者中肆虐。 寻求一线生命力的受灾者纷纷投身突破国王的军队,让农民战争野火无限,叹息“贼杀不了”的明军将军留下另一具尸体躺着的修罗战场,走在这条路上随时倒下的乱世,显然有人将阵亡者的尸体 从1629年开始4次入驻的“后金-清”势力,为了最大限度地破坏明帝国战争的潜力,有意识地在华北全体组织大规模的掠夺、破坏、屠杀行动,这样的人为恐惧除了引起上述尸体穿越原野的瘟疫之源外,还引起了本能的恐惧 邓拓的《中国救荒史》统计的中国历代疫病的发生次数:周代1次、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 《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的统计数字比这个数字大得多(明代176次,清代197次) 仅从统计数据来看,明清两代疫病的发生次数最多,其中越接近现代的王朝,历史文献资料越多,越有完备的因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明代以来人口增加,工商业迅速发展,胡熙庸线以东的人口密度增加, 崇祯3年,明朝人口达到高峰,总人口1.7亿左右,人口最多的浙江省达到2485万人,人口密度为246人/平方公里,京师地区(北直隶)每年遭受兵祸(乙巳变化)和瘟疫,但依然有1000万人 在古代的卫生条件下,这个人口密度为大规模传染病流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其中由于地理和气候的原因,北方的公共卫生条件比南方差,北京市大街上有半尺多的浮土。 其中混杂着人畜粪便,每次刮大风天地都变黄无法分辨太阳和月亮,遭遇天灾,容易引起严重的传染病危害。 万年官员指出:“京师住宅严格,市里屎多,五方人,繁杂的杂处,还有苍蝇虫多,每次热,都没几次生说话,下点雨,即有浸灌的患者,所以疟疾疫情,还是绝对没有。” 明代最严重的瘟疫是这场“大战、大灾害、大瘟疫”的复合爆发。 这次大瘟疫始于崇祯9年( 1636年)李自成在陕西稳定中打败明榆林总兵后,“大瘟疫大机、瓦塞堡瘟疫尤为严重”。 崇祯十年,张献忠攻陷湖北玫瑰春、黄石,蹂躏江西九江,引起当地饥荒、大瘟疫。 崇祯11年,是南直隶太平府的大瘟疫,死者非常多。 崇祯12年,山东历城,齐河大干旱,很快就得了大瘟疫。 崇祯从9年到崇祯13年,河南省连续5年遭遇大旱。 官兵、流贼轮流屠杀人民,情况极为悲惨:“五载干旱蝗虫,兵贼燃烧掠夺,烈性瘟疫横扫,民死于兵,死于贼,死于饥寒,死于瘟疫者,百不存一二。 幸存者吃草根树皮,父子兄弟夫妇残食,骨头过郊野,庐舍邱墟 “明朝灭亡前几年,这场惨烈的复合式灾害每年都发生,有时一年几次,范围也扩大了,人们也逐渐从这样越来越频繁的瘟疫中隐约发现了其中的规律 “年凡贼(李自成军)经历的地方都是大瘟疫,不经历的不是瘟疫。 “当时人们注意到的是灾害、战争、瘟疫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灾害引起饥荒和瘟疫,迫使被郡制束缚的农民为了生存而流亡,没有避难所就不自觉地加入闯王大军,开始大规模异常的人口大移动,老实说 这也是李自成的大军长年逃往疫区的原因——无论他的军队因疫情死了多少人,只要军队本身一直在运动,就可以陆续得到兵源补充。 这成为了某种自然选择的机制,他的军队中哪支军队总是没有战死或病死的中坚力量,也许是因为这样残酷的环境获得了对某种或几种疫病的免疫能力。 使他的军队不受严重的军事失败,结构总是完善。 但是,长期停留时,不要受到疫情的严重打击。 山海关战役失败后,突入军不是急于利用北京城坚固的城防和城头的大炮,而是和清军一起撤退的。 因为我承受不了瘟疫引起的减员和潜在崩溃的风险。 然后,大明朝的官府和军队一边感叹“贼杀不了”,一边无奈地把饱受灾害和瘟疫折磨的人们送进了侵略军。 这支军队对经过的地方来说一定是瘟疫大军。 “所有贼(李自成军)经过的地方都是大瘟疫,经验者不是瘟疫”是入侵军当时携带的强烈传染病的真实写照,“经验者是大瘟疫”证明传染性很强,“经验者不是瘟疫” 除了这种行军的传达方法,好杀的张献忠还用特别的方法传达瘟疫。 “3月将贼献给蜀国,积尸复河,臭味几十里,1月去。 年瘟疫,死者十分之七十八。 “张献忠进攻四川省的战乱受害者尸体被扔进长江,顺江漂流到湖北省领土,堆积在长江拐角处的湖北宜都县江面上,引起了严重的疫情。 明代灭亡前两年,瘟疫迅速发展成严重的威胁统治。 “京师从春祖秋大瘟疫,死尽田地”“大瘟疫,南北几千里,从北到塞外,南超过黄河,十室生一脱者”,在文案开头百日鬼行市,出现了呼啸语人间的奇怪形式。 官救、自助、天救从万历后期开始瘟疫持续,引起了整个社会的重视和恐慌,但受古代卫生条件的限制,从当时的政府到民间,没有预防瘟疫的水平和能力,对大部分人来说,被感染的命运是病死(大部分)和自身 这是当时人们对传染病的认识度、公共卫生条件和医疗水平共同决定的。 自然灾害引起的饥荒是引起疫情的主要原因,明代灾害救援的粮食仓库制度有官仓、备用仓库、义仓、社仓等,粮食救济在某种程度上使受灾者留在原地减少流动,从侧面控制疫情,恢复灾后疫情后的生产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灾害救援准备制度逐渐失效,粮食仓库普遍没有粮食或完全废弃。 特别是明清战争开始后,全国物资和经费开始陆续送到辽东的战争黑洞,连各地平定农民战争的军队粮食都不能保证,平反军缺乏粮食时,往往掠夺附近的粮食仓库,进一步降低灾害救援准备制度 电影《大明强盗》中孙传庭潼关检查粮食的桥段只是结束气象的一景,连军粮都不能保证,受灾者接受救济的范围和程度,自然可以知道。 与粮食仓库制度同样衰退、失效的是明代的传染病防治制度,明代在地方设有医学和惠民药店,是主要的疫病防治机构,医学是负责培养医学人才的学校,惠民药店为疫病人们免费或廉价地提供急救服务和药物 但是,在很多地方,两者形状相似,关联机构也没有确立,在明中期的疫情中惠民药店已经发生了“官无药饵,民多死”的现象。 万历十五年,朱维藩上奏为了疫情对策恢复了各地的惠民药店,神宗准奏证明了当时惠民药店被大量废弃。 到了明晨末,还没有正常运作的惠民药店,除了废弃和医生逃亡以外,有些惠民药店因疫情所有员工都生病死亡,陷入了悲惨的状况。 在这种情况下,平民正式得到的医疗救助完全依赖于生活区域和运气,整体水平很低。 与地方相比,京师的情况比较好,但不乐观。 明代在中央设有太医院,为皇室提供医疗服务,疫情发生时,也参与社会急救治疗。 但是,这种“恩赐”式的急救治疗,实际上很少有幸运能让人开心。 以万历十五年( 1587 )年的大瘟疫为例,神宗命令“太医院选委医官,多药,分五城开局给药,因病救药”,治疗患者的“一万六百九十九人”和受瘟疫的人有多少? “经历过疫情的人有四十二县六十多万户”“民死十分之四”,接受急救治疗的患者不到1 %,但这一万多名幸运儿中有多少真正被“治愈”了,还不知道。 明末的政府救济防疫制度全面不起作用的背景是明代银不足的困境。 从1550年到1644年,从西属美国经由马尼拉进口的白银和日本白银累计超过1亿2千万(据学者称,这里取最低值),完成明朝的“银纸币易位”,促进经济繁荣,同时 “白银红利”的副产品通货膨胀和投机活动的作用也开始凸显。 农业社会没有太多的投资渠道,商人和地主拿到白银后,只把一小部分投入再生产,大部分用于贵金属储藏,进口的白银已经超过了整个社会的总诉求,但由于没有真正的流动性,社会的总资产明显增加 用很多货币追踪总量没有太大变化的实物的话,进口性通货膨胀是不可避免的。 物价上涨的最大受害者是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农民的苦难和农业的残骸,动摇了以前传到农业帝国的根本。 大明必须消耗越来越多的白银来驱动不堪重负的战争机器,除了其糟糕的税收政策外,大明尽管在白银之海,但始终处于银荒的困境。 在开头提到的崇祯16年( 1643年)的京师大瘟疫中,朝廷为太医院预防瘟疫支付的钱是“白银一二”,为掩埋死者尸体而收敛的只有两万两。 惠民药店没钱买药,不能吃药的现象,只是银荒困境的许多结果中最微小的东西。 与难以期待的“官救”相比,民间的自助反而是可靠的,这是在频繁的疫情中,医生和民众通过对疫情的注意,总结了预防管理知识丰富的结果。 除了前面提到的“大战、大灾害、大瘟疫”三者之间的关系外,当时的人们对人口密度和疾病感染的关系也有很深的认识,在明人吴遵所著的《首次录音》中,救济救济救济时必须选择“宽敞清洁的场所发出辰巳,下午发出。 “免疫回避”成为社会共识,也影响了政府,在疫情期间政府有条件让人们集体避难,释放监狱囚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疾病的传递。 由于官方救助的无力,政府经常鼓励人们粮食、出资,捐赠的物资为用药、煮粥、埋骨等救援活动提供部分或大部分资金保障,这种做法在应对局部疫情时有效,当地富人 大家、富裕阶层的救援积极性不高,协助不够的情况下,像“大明强盗”的孙传庭一样使用威胁和强制手段“借钱”的也不少。 但是随着疫情范围的扩大,震级的增加,大户家也经常关门生病,家没落的命运,救不了别人了。 对大量疫情病例的细致注意,提高了医生对传染病的认知和防治水平。 例如,吴有性的“疫论”除了没有现代微生物学和病理生理学外,瘟疫是由天地之间的“杂草、异气、疥癣气体”引起的,不同气体引起的疾病被指出“分别随其气体而生病”。 根据大量临床经验,吴有性被限制在时代认识水平上,在对病原机制认识错误的情况下,通过很多细节的注意总结接近正确结论的经验,对传染病的防治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特别是他在疫情传递方法的评价“邪自口鼻入”上” 这些评价在隔离的基础上提出了防护理念,接近现代传染病防治思想。 但是,正如电影《大明强盗》中所表现的那样,吴有性(吴又可)这样的医生当时只是战争混乱中的沧海一粟,人命如草芥乱世,他无法起到扭曲干坤的作用,其真意也没有广为流传。 受古代传来的医学“辨证”、“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思想的影响,当时认为同样的疾病发生在南方和北方,所以经验不通,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需要不同的治疗方法。 类似于“疫论”的宝贵经验,不能成为广泛共识和防治的基础。 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近代,以1910年的东北大鼠疫为例,在1894年的广东大鼠疫中,岭南中医写了《鼠疫害微》、《鼠疫约篇》、《鼠疫汇编》等著作,其中有关于预防管理的洞察(比如吃猫, 除了官救和自助,“天救”是所有营救方法中最重要、最有效、最残酷的。 所谓天救不过是三种方法。 等待疾病病原体适当传达的第一个季节过去了,疾病的个人和死亡,或者治愈,瘟疫自然消失了,历史上大部分瘟疫都这样消失了。 二是等待疫情造成大量人口死亡,疫区人口密度下降到一定程度后,疫情的速度自然减缓消失。 三是个人幸运地在疫情中自我治愈,获得了某种免疫力。 “天救”的过程很残酷,但由于乱世大部分人的命运,很多人在1644年发生了“明、清、冲”三者的战争。 为什么明军和侵略军受到当时北直隶大瘟疫的重大打击,清军影响很小,但观察不到,满清。 清军来自关外,对关内疫情敏感性高,而且满洲总部人口少,战兵少,不堪巨大损失。 这非常敏感,一边让以吴三桂为首的前明降军追踪侵略军,一边尽量在华北制造恐惧,进一步淡化人口密度。 另外,清军火葬阵亡者煮饭(焚烧死者生前的遗物)的习惯也限制了疫情的传播。 尽管无官、无兵、无人认识到在瘟疫中隔离的重要性,官员作为防疫的主要负责人,面临着救人与拯救自己矛盾的困境。 没有防护条件的,官员为了履行职责,不得遭受瘟疫。 崇祯14年为北直隶大瘟疫、顺德知府(北直隶顺德府)、长垣(北直隶大名府)、大名(北直隶大名府)、曲周(北直隶广州)。 除了传染病的死亡,许多官员为了自助选择深居简,导致当地行政效率下降和政府职能失控,从崇祯9年到崇祯17年连续战争大瘟疫动摇了明帝国整个北方的统治基础和行政结构,后者 崇祯8年,明朝将军尤世威战斗李自成时,军队长时间住宿在疫区引起大瘟疫,因此作战失利主不仅受重伤,军队也直接崩溃。 大军开始直接越过卢氏,奔向永宁。 经过1643年冬至1644年春的大瘟疫,李自成兵来到北京时,北京城防完全崩溃,行政系统混乱,上下指挥不善,侵略军已经进城,锦衣卫还逮捕了散布突破王入城“谣言”的“妖人” 可以说是混乱。 除了“没有官员,没有士兵”的绝对国外,瘟疫还沉重打击了明王朝统治的合法性。 关于疫情,上天警告人类统治者的观念根深蒂固,历代统治者也把上天的祈祷作为应对灾害疫情,提高自身合法性的一种手段。 如果这个祈祷偶然“有效”,那肯定是“有效”的。 就像开头提到的崇祯16年( 1643年)的大瘟疫一样,崇祯进行的法事最终毫无用处,失去民心,让舆论结合这次祈祷的失败和1644年发生的满清入,大明气尽,上天不回应皇帝的要求,大清天错 这个“瘟疫心理学”对笃信天人感觉的读书人最有效,最终成为了王朝兴衰中选择阵营的重要领袖之一。 明末的瘟疫只是古代瘟疫的缩影。 在古代,消灭瘟疫最有效的手段不是防治,而是天气、屠杀和烈火,在《大明强盗》中吴有性对孙传庭说。 “州长控制疫情的方法真的比吴有效。 “既是讽刺,也是没办法,也是事实。 老百姓的命运就像稻草,随波逐流。 (本文来自澎湃信息,越来越多的原始信息请下载“澎湃信息”APP )
标题:热门:“万户萧疏鬼唱歌”:明末大瘟疫中的众生相
地址:http://www.cfcp-wto.org/cfzx/1727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