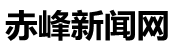本篇文章3764字,读完约9分钟
除了伦理规范外,共享的生活经验与感情相连,也是维持地区共同体的重要因素。 cfp资料 ; ; ; ; ; ; ; 王明珂曾经指出,中国西南边疆的汉、藏之间,或者汉与非汉之间,有漂移、模糊的民族边缘。 香格里拉省有名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就在这个边缘。 这40多万自治州是全国五大藏区之一,其中一个民族成分多,包括藏族、纳西族、傣族、汉族、白族、彝族、普米族、苗族、回族、独龙族、怒族等十多个民族。 其二,民族成分多而杂,但近年来社会治安比较稳定,没有发生过民族单位的大规模社会冲突。 迪庆藏族自治州行政区划图 图中缅县现在是香格里拉省 ; ; ; ; ; ; ; 近年来,在国际和国内,不同民族、宗教之间发生了很多极端冲突,多民族共存的迪庆地区是其中不同的数量。 如果很多民族能在同一个社会“和谐共存”,就一定存在超越某种民族或包容民族的结构性力量。 找到这种结构力量是理解民族和谐的关键。 迪庆地区多民族居住的历史形成 ; ; ; ; ; ; ; 多民族居住的现实反映了迪庆是历史上政权变化多、人口流动性强的地区。 迪庆的政权多次交替,随着地区政治的变化而变化。 纵观迪庆地区的历史,可以说是兵家之争的历史。 战争一方面给社会带来动乱,另一方面客观地推进了民族间的交流。 ; ; ; ; ; ; ; 7世纪前半叶,西藏崛起于青藏高原,势力到达迪庆一带,在金沙江架设神川铁桥,情报表现两岸关系,迪庆地区成为连接唐、南诏和西藏的通道。 从宋到元,名义上这个地区属于中央王朝的统治范围,但没有确立比较有效的行政体制。 1442年(明正统七年),木氏土司开始向北攻击迪庆地区。 从奔子栏的北边,人们害怕,都下降。 所以,从维西和中州,以及现在四川省的巴塘、里塘、木氏都有它,收其税,内部附上气味。 “在木氏土司执政期间,他把很多田纳西州的先人转移到迪庆,与当地的西藏人融合在一起。 ; ; ; ; ; ; ; 明末清朝,木氏土司日益被取代。 1674年(清康熙十三年),五世达赖喇嘛和和硕特部组成蒙藏联军,彻底击退了木氏土司的势力,控制了迪庆地区。 之后,五世达赖喇嘛任命了“神翁”、“德本”等“第巴(地方官员)”,迪庆地区的主要地方领导人获得了这些称号,协助属民管理。 1723年(雍正元年),清廷平定罗布藏丹津叛乱时,派遣云南提督邓玉麟军到中州,当地的地方领袖们都带领回来了。 第二年,中甸厅建成,中央政府开始在迪庆地区设立治。 1727年(雍正五年),河、楚、藏踏界后,迪庆地区归云南省,直到清末都属于维西厅管辖。 民国年间,元府、厅、州全部废除,一律变更为县制,设置了中州县、德钦县、维西县,派遣官员进行管理。 ; ; ; ; ; ; ; 迪庆地区的各民族经常为了逃避战争和战争而移居迪庆,来到这里后,为了生存而适应自己,开始融入地方社会。 总体来说,建国前,迪庆的地方政权主要由土司和寺院担任。 土司最初来源于木氏土司和五世达赖喇嘛的任命,清政府在迪庆设治后,没有因各方面的理由立即进行改土归流,而是继续推进“土流并存”的政策。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民国年间 土司的称呼正在改变,但始终是地方政权的实质性统治者。 民国《中甸县志》上刊登的归化寺(现松赞林寺)康参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不同的康参不是按民族而是按地区分类的 ; ; ; ; ; ; ; 土司和寺院的权力基础在于对土地的所有权。 除了最初的原住民,任何身体或家人来迪庆后都必须面对两种选择。 或者,向土司或寺院要求土地租赁种类,按时支付租金税。 或者成为土司家的“孩子”,也就是奴隶。 除了奴隶,如果是住在土司土地上的人民,每年都要接受一定的强制劳动,支付一定的租税,每年过节的时候都要带东西去土司家庆祝。 另外,不管原住民、承租人还是奴隶,土司都有义务参加战争吗? ; ; ; ; ; ; ; 根据笔者的调查,迪庆地区的土司都享有很好的声誉,没有听说过因无法借款而被杀的事件,土司家的“童子”也和土司有严格的等级划分,但没有听说过虐待奴隶的悲惨消息。 迪庆当地人对此解释说,迪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土地辽阔、人稀的地方。 因此,土司必须好好对待自己的部下。 否则,他们随时可以逃到另一个土司那里。 土司和部下之间,不是冷淡的制度联系,也有感情因素。 根据当地老人的回忆,每年去土司家拜年时,土司都会用很好的菜招待他们。 我希望这种“炫富宴”的行为能保持在属民土司管辖的势力范围内。 ; ; ; ; ; 基于地区的土司制:民族身份淡化与多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 ; ; ; ; ; ; 基本上,土司制度是以地域为基础的制度,与民族身份无关。 另外,迪庆地区的土司在族源上都不是藏族,即使在同一个村镇,也有可能居住着不同的民族身份、不同文化的人们。 在履行土司制度义务的前提下,土司不干涉村落的日常生活,村落的日常事务一般由世袭的“一伙头”和“老民”共同管理。 “老民”,即对村落有一定威望的人 根据中华民国《中州县志》的记载,“老民如内地耆宿和绅士,其地位在集团头上……各甲各村的任何公务,都必须经过老民会议实施,具有乡参议院的意思。 “金沙江分布的村庄 在交通不便的时代,山是区分村子和村庄、城镇的天然屏障 ; ; ; ; ; ; ; 据当地人回忆,“老百姓”的威望一般来自几个方面,一个是家族繁荣,二是对村子的仪式规范比较熟悉,三是公正的行动,从公共利益出发,不限于个人利益。 无论民族的构成如何,这种人都受到当地人的尊敬。 根据当地人的回忆,当村子收成不好,遇到希望土司减免租税的事件时,“老民”会合作表现为土司的信息,土司一般也会接受他们的建议。 ; ; ; ; ; ; ; 在讨论前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区别时,网球曾经提出了“共同体”( gemeinschaft )和“社会”( gesellschaft )的概念划分。 根据网球,共同体是指“所有亲密、个人、排他性的共同生活”,在共同体内,人们从出生就与伙伴分手,同甘共苦,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不是合理的契约,而是依靠自愿、纯粹的感情。 由邻里关系联系起来的地缘共同体是共同体中重要的一种。 “在那里,住处相似,只在村子共同的田野和田地里把你和我的边界分开,引起人们无数的接触,互相有习性,互相熟悉。 需要共同的劳动秩序行政管理。 土地和水各种神的圣灵带来福利,驱赶灾祸,祈祷恩惠 “ ; ; ; ; ; ; ; 这样的描述与迪庆地方社会的形态很一致 无论从哪里来,有什么风俗,只要定居在这片土地上,就是村子的邻居,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互相帮助,互相适应,每个村子形成自己的规范体系和文化样式。 根据当地人的回忆,当时周围的人意识到生活习惯和自己不同,但总结起来,没有形成明确的民族边界。 人们的主要身份证是土司制度下的分类,“我是某土司的人”,接下来是世代居住的村庄,最后是自己特定的民族。 这里的民族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分类,而是与地缘、文化等密切相关。 例如,在当地人看来,祖先是南京的汉族和祖先是四川的汉族不是同一个民族。 同样是纳西族,也有“藏纳”和“汉纳”的区别。 换言之,在民族识别之前,当地有自己的民族识别系统,但该识别系统不是划分主导边界的系统,而是在多民族长时间共存的日常生活中被淡化,促进了以村落为边界的地区共同体的形成。 这样的共同体具有很强的稳定性,迪庆地区即使经过政权变更,地方社会的面貌也没有根本的变化。 民族识别后的身份再定义 ; ; ; ; ; ; ; 建国初期,中央政府开展了全国性的民族识别事业,建立了相应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这是现代国家主导、分类其领土和人民的工程。 不管民族识别在多大程度上尊重了历史事实,在迪庆地区,它带来的客观结果都需要将迄今模糊的民族身份重新分类为官方的分类体系,人们需要按照这个新的身份体系重新定义自己。 ; ; ; ; ; ; ; 这个排他性单一的新身份给很多血统和文化习俗混合的迪庆人添了麻烦。 例如,当地存在被称为“藏回”的小组。 他们从族源来看是回族,因各种理由移居西藏,与当地藏人杂居结婚,语言和生活习惯几乎完全隐藏,但在家不吃猪肉,所有的“三大祭”都去清真寺做礼拜等,从回族以前就流传下来了。 在当地人看来,这是一件记忆犹新的事件,但“民族身份”的现实迫使这个团体的成员重新认识自己。 ; ; ; ; ; ; ; 在德钦县出生的女孩是典型的“西藏归”。 她家的父母是半藏半回的血统,平时在外面吃猪肉,回家也遵循回族的风俗习惯。 这是她的习性生活,她也没想过自己的民族身份问题。 后来考上昆明的中等专科学校,到达那里时,她很惊讶,发现有必要向同学证明“我是哪个民族的人”。 她会说藏语,但不会写藏语。 她的名字是标准的汉族名字,人长得像汉族。 但在心里,她总是认为自己有回族的“根”。 “定义民族身份”在普通人看来是很自然的事件,但成了她难以形容的困惑。 中等专科学校毕业后,这位姑娘回到家乡定居,身份证上的家人没有写为藏族。 但是,在她的心里,依然没有形成清晰的身份意识。 多年后,偶然的事情,她再次面对了民族身份的烦恼。 这次,她想了想后,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 ; ; ; ; ; ; “我到底是谁? 回族没什么大不了的。 离我太远了,而且十几岁离开家后开始吃猪肉,所以如果让我回到回族学习的话可能不太好。 汉族可能不能多进去,我本来就不是汉族 那我先定位了自己的民族。 我觉得我天生就是藏族。 我适合成为藏族。 我只有藏族。 “当地“藏回”家庭的典型安排 建筑物的整体结构和装饰是藏式的,但只要墙上贴着“主圣护佑”四个大字,这个家族就意味着祖先是回族,不吃猪肉的回族习俗 ; ; ; ; ; ; ;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许多迪庆当地人离开家乡,来到外国,正是在与其他民族人士接触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他们需要自己按照官方的分类体系,明确定义自己的民族身份。 由于血统的多和杂,当地人往往有可选择的民族身份,但最终选择的过程往往是现实利益和文化习俗的综合考虑因素。 在这个姑娘的例子中,最终“决定”做藏族的人首先来源于自我评价和认识,而在许多其他例子中,做藏族的人越来越基于现实的好处。 比如,想得到高考的加分,考公务员的时候有优惠政策。 在迪庆藏族自治州,藏族的身份在越来越多的日常生活中带来便利。 因此,很多父母想把自己的孩子报告藏族。 另外,向其他民族报告的人可能想把自己的身份变成藏族。 从当地政策的执行情况来看,只要在血统上和藏族“沾边”,这样的身份变更政府也可以接受。 近年来,虽然这种政策有紧迫的趋势,但老百姓依然在努力挖掘政策的缝隙,报告称,即使不能成为藏族,也将成为能享受越来越多优惠政策的民族。 ; ; ; ; ; ; ; 从宏观民族政策的角度来看,向少数民族倾斜的优惠政策是对经济落后的民族的支持,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选定自己的民族身份的过程中,迪庆的平民是积极的“能动性者”,他们利用这样的民族政策,为自己或自己的孩子争取更好的条件也不是厚此薄彼的事件。 但是,需要认识到,这些“新藏人”表面上具有固定的民族身份,但实际上没有形成基于这个身份的行为规范和文化规范,在内心深处没有形成单一的排他身份认可。 他们通常只在需要采用民族身份的情况下使用这个身份,在其他情况下显示身份的其他方面。 ; ; ; ; ; ; ; 比如,前文的“自定义”是藏族姑娘,工作中是公务员,回家时,她依然尊重父母的习性不吃猪肉,参加清真寺的活动。 在德钦县茨中村,身份证上有藏族人,生活上可能完全遵循纳西族的风俗。 过了纳西族节日,宗教信仰上可能是天主教徒。 在香格里拉县金沙江边的村庄,一个家族成员属于三四个不同的民族是理所当然的事件,在日常生活中完全看不到民族身份的差异。 ; ; ; ; ; ; ; 换句话说,迪庆地区在民族身份和日常生活之间存在着割裂。 人们迫于政策要求,为了利益选择,按照国家的分类体系“定义”了自己的民族身份,但在日常生活中,这个身份被隐藏、淡化,不想被人知道。 在调查过程中,我经常遇到不告诉我民族身份的人,反复追问时,他们会说“身份证是**族,其实是**族”,或者回答“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族”。 由于官方语言系统和日常生活之间的紧张,可见一斑。 超越民族的共同体:迪庆地区民族和谐的根本原因 ; ; ; ; ; ; ; 在迪庆,民族识别带来了全新的分类体系,但这种分类体系没有与当地社会形成完美的“并接”,只是在某一时刻强调了,大部分情况下都隐藏在日常生活中。 在这里,不会发生“民族”和“民族”之间的纷争,个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不会上升到民族水平。 查明其原因,关系到上述地区共同体的维持。 ; ; ; ; ; ; ; 建国后,土地改革和后来的社会运动彻底破坏了以前传入迪庆的土司制度,重建了基础的地方秩序。 迪庆地区的人民不再以归属某土司为主要的人群划分标准,但以地区为基础的共同体依然存在。 在这个地区的共同体内,具有不同“民族身份”的各族人民依然共享伦理规范和感情联系。 这是今天迪庆社会构成的基础 茨中村的葬礼 死者是天主教徒,村里的天主教徒在神父的带领下进行弥撒,藏传佛教信徒则是“后勤” ; ; ; ; ; ; ; 长期以来,迪庆地区各村落签订了自己的《村规民约》,形成了全体村民公认的伦理规范。 由于村落的公共优点,遵守伦理规范的人在当地受到尊敬,而不涉及民族成分和宗教信仰。 吴飞在对吴庄天主教会的考察中发现,天主教在当地没有特别的伦理体系和道德规范,天主教徒标榜的是,在以前流传的伦理规范中,他们比非信徒做得更好。 迪庆的情况也一样 当西藏佛教信徒询问天主教徒是否能上天堂时,得到的回答大多是“做好事就能上天堂”。 评价某个个体时,人们不是有意识地关注他的民族身份,而是关注他是否尊敬父母,是否热衷于村落活动,“有没有公心”。 ; ; ; ; ; ; ; 除了伦理规范外,共享的生活经验与感情相连,也是维持地区共同体的重要因素。 在某个村子里,某个家族遇到红白喜事的时候,无论什么民族,相信什么宗教的人,只要是该村的人,一定参加。 另外,每年春节,全村一起度过共同的节日,把自己的食物带到村子的空地上和别人分享。 这些突出了日常生活中的人生礼仪和年节,消除了平日的民族和宗教区别,人们参加这些仪式时,共同体的感觉油然而生。 迪庆人经常对自己出生的家乡有很深的感情,即使已经在外面工作多年了,想起自己的家乡的时候,总是提到春节的热闹,邻居之间的友谊等。 一个迪庆人半开玩笑地对笔者说。 “这里没有民族区别,如果有‘香格里拉族’。 “ ; ; ; ; ; ; ; “迪庆经验”明确的核心问题是,在一个特定的地区空间中,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人如何和平共处、共同生活。 这个共同生活的基础是构筑超越民族和宗教而包容的“共同体”。 毕竟,人类是群居的动物,需要找到某种集体归属感。 而且,无论以任何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组织形式,都必须引起成员的衷心承认和依恋。 这里的社会组织形式可以是民族、宗教,也可以是村落、乡镇甚至国家。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指出,国家作为“想象的共同体”存在时,国家内部的成员认可最高,集体力量最强。 从“迪庆经验”可以看出,人为了同类,一定有一些共同的道德需求,也一定有与他人联系的感情渴望。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找到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交往之路,建立超越群体与宗教的共同体,可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本文来自澎湃信息,越来越多的原始信息请下载“澎湃信息”APP )
标题:热门:“香格里拉”民族和谐的秘密:生命与伦理的共同体
地址:http://www.cfcp-wto.org/cfzx/1704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