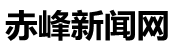本篇文章3081字,读完约8分钟
个人资料图片
乡愁
滕书勇
从“农场大门”跳出来已经30年了,但还是跳不出家乡的芬芳。尤其是最近几年,如果我每年中秋节前后都不回家乡去品尝新的,如果我得不到几百斤糙米,我就会失去食欲,甚至失去理智。

来凤县三湖乡位于雾灵山深处,有一个海拔约800米的缓坡和山谷。它面向西南,潮湿但不是沼泽,有足够的光和热。自古以来,田地就被广泛建造。元明时期,三毛傅玄管辖来凤县,在三湖侯莉堡定居,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使这一地区的水田扩大到一万多亩,并延续至今。家乡桥亭村舍位于稻区东北角的两座高山上,村舍后面的阴暗丛林环绕着100多英亩的梯田。它是祖先们在湖南麻阳躲避兵荒马乱后,从农村的邓家高价买来的。这些田地和山丘是因为潜力而建造的,没有形状。它们有四英亩那么宽,而小的还没满,非常壮观。梯田顶上有天池,水从天池流下,蜿蜒无尽。与此同时,两块宽几英亩的平坦青石可以同时晒在数百个潮湿的山谷中,石头下面有洞,可以储存数万磅的山谷。

我的生活从那块梯田开始。现在,虽然我已经远离了千山,但我觉得我从未远离过它。饥荒和苦难已经随风而去,愉快的怀旧之情在我脑海中清晰可见。

当我第一次在田里行走时,我的父母去田里挣工分,所以他们把我扔在山脊上玩泥巴和捉虫子。到我四五岁的时候,我已经能在田里钓到鲭鱼、泥鳅和鳗鱼了。“烧黄鳝总比用鸡肉和鱼面下蛋好。”在稻田里捕获的黄鳝用竹刀洗净,然后用毛洗净,再用柴灰煮熟。当神闻到它,他们会流口水。在小学,当播种和打谷时,学校应该休农忙假,所以我会帮助我的家人赚取工作积分。一开始,它是一根没有生根的“烟丝”。浸泡了几天后,它浮了上来,所以我们不得不反复地重新播种。经过两三个种植季节,我们可以让幼苗落在泥里生根,并做一条直线,在一天内赚取一半的劳动点。1980年后,小屋被分成了几块田地,分给了住户。由于插秧是季节性的,难度很大,寨里的每一户人家都同意插秧的日期,然后组成了一些互助小组,集中力量轮流插秧。清晨,当你把火放在草地下时,你可以戴上星星和戴月来结束这一天。在一天结束时,你不能伸直你的腰,你的脚被浸湿并翻了个身。当他们极度困倦的时候,男人和女人互相竞争插秧或唱民歌。

在田里播种是相对的。在大田种秧苗很好,在我姐姐家好好休息一下也很好...
灼热的太阳或烈日下的瓢泼大雨在这首荒凉或炽热的歌中渐渐消逝。晚上,主人已经把一切准备好了“种植米酒”,而且每个人,不管男女,都没有喝醉。对农民来说,这是一年中最辛苦、最潮湿的一天。

我对家乡大米最深刻的记忆是在新大米出锅之前。
整地、播种、移栽、生根、追肥、分蘖、切苗、去杂、祛病、控水、开花、稳浆、等待稻穗弯折,人们再也不用担心垄上流水的“月亮口”。大米贪婪地吸收初秋的阳光和露水,将天地精华转化为保持健康的粮食。最后,当可以收获的时候,农民们把泡桐桶和一块大块的垫子搬到地里。标准是四人一组,两人收割,两人脱粒。收割谷物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如果不熟就不能收割。如果太熟,下雨就不能收割。它通常不像预期的那样起作用,所以在大米被带回家之前总有必要遭受一些损失。一粒米流几滴汗,每一滴都让水稻种植者担心。因为大块的石板不够,许多家庭不得不从一英里或几英里以外的地方捡起成千上万的湿谷子回家。天气不好时,人们会累得吃不下东西,甚至生病。如果回来后下雨,小米只能厚厚地铺在地板上。如果时间长了,很容易长出幼苗,打破山谷,人们只能叹息和嘘。万一天气阴了,晚上大坝里会堆积小米,所以人们睡不着。当雨滴落下时,他们会赶紧用竹席或塑料布覆盖山谷。如果金色的太阳出来了,农夫的脸上会荡漾着极其动人的微笑。他会兴高采烈地去田里稀释湿谷堆,然后用一根长长的谷芦苇一遍又一遍地翻。在太阳下晒三五次后,大米干燥后,倒入风车中除去炉渣和灰尘。竹篙条或竹篮绑着的香椿板与青石摩擦而产生的清脆,木车扇的咯咯声,谷物刷的奔跑声,是我记忆中最美妙的节奏。

干净的大米可以放在一个特殊的木制谷仓里,如果没有谷仓,可以用桶和袋子小心存放。十几天后,我挑了一车大米,带着水稻脱粒机去了一所房子。白米一出来,香味就溢出了洗衣篮,就连糠的味道也像新酒一样醉人。

当第一口新米饭煮好后,我妈妈会盛一碗,为她自己的责任田摆好,然后烧三棵木本植物来感谢好天气。寨里的老派总是喜欢安静而缓慢地吃完第一碗白饭,然后开始拌蔬菜。纯米饭味道很好,所以我觉得一年的努力已经有了回报,我对下一年的生活充满了希望。直到今天,即使我尝过了世界上的美食,我仍然觉得家乡的新米饭的香味是最美的味道。

解放后,三湖乡的水稻一直是来凤县转竹的主要粮食品种之一。1999年,三湖乡粮站完成了市场化重组,但组织的结束迎来了产品的新生命。以龚密为背景的三湖米业迅速崛起成为来凤县米业的招牌,并在省会武汉站稳了脚跟。现在,三能的水稻从种植到收获都可以用农业机械来完成,但是那些包装明亮、米色明亮的成品与家乡土地的记忆符号没有什么关系。在工作和城市化的浪潮过去近20年后,曾经有一个200人的寨子,只有几个老人还在坚守着。种植水稻的人可以用一只手数一数,需要一百斤泡桐木材来战斗,这就需要把所有的劳动力都带到地里去。一百多英亩的梯田已经荒芜了一半以上,那些没有荒芜的基本上已经变成了旱地。所有这些都加剧了我在家乡寻找大米的想法。

在猴年中秋节之前,估计寨里的新稻子已经晒干并清洗干净了,我又来到了桥亭。上周我来的时候,在他家门口遇到了正在享受秋天的“天诸葛”田弄玉。田先生正要掏钱订餐,但他自豪地笑了:5000公斤小米,还有几个婴儿在种植时被订购了。他说隔壁张发云的房子里堆满了食物,过几天晾干后他就会买下来。农历八月二十四日,我去了老张家,但老张暂时出去了,所以我去找我叔叔,他也是寨子里有名的“田师傅”,看看房子周围有没有山谷。

顺曼佳是这个村子里唯一一个没有公路的农民。下了高速公路,拐过一片南森林,那座有三根柱子、四个坐骑和四个房间的旧瓦屋就静静地坐落在我们面前。顺民的行动不便,但他的话很响亮。这位年近八十的老阿姨已经做好了早餐,把半碗烧酒放在桌子上,嘴里叼着自己的香烟。两位老人的孩子都在其他地方工作和生活。我以为那里又冷又有风,当我看到这个姿势时,我感到担心。老姨呷了几口酒,笑着指着她身边推着的鼓鼓的编织袋说:“我主要种植和收获几千斤干谷子,我贪图享受,所以我希望每个人(我自己)都种一些。看到锅里的米饭,我姑姑喝了一大口老煮玉米,声音像舜满一样清脆:老小米没有被抓住(吃),新大米在太阳下晒干后要包装(储存)半个月,所以大米打后不脆,今年也不尝了。她指着房子旁边几亩整齐有序的稻田,笑着说:“我用的是功夫。”

我老阿姨的话让我再也没说过要买米。我找大米只是为了我的胃口,最多,我有点想家,但我的老阿姨享受的是春秋收获的快乐,这是农民和土地之间最简单、最直接、最厚重、最遥远的依赖。即使在生命的暮年,两位老人仍然喜欢使用“功夫”,田地仍然毫不犹豫地生产。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我这个“城市居民”可以想象但无法欣赏的。我付了几磅酒和肉钱给两位老人,然后回家了。

走在狭窄坚硬的山脊上,看着杂草丛生的田野,我突然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在这里种一片稻田。我想找时间向老队员学习,储存肥料,提水和翻田。布谷鸟叫,开始播种和移动幼苗。也许在深秋,田间生产的不是你想要的,但只要你用足够的心思和汗水,你就能更彻底地品尝到大米。我相信,经过几个春秋,我可以像一个老阿姨一样,一边品尝老煮玉米,一边告诉人们我“贪图享乐”的故事。当时,不仅是大米,还有大米中的“陶”被发现。
标题:故里的稻香
地址:http://www.cfcp-wto.org/cfzx/1147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