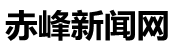本篇文章5367字,读完约13分钟
原创詹姆斯道琼斯理想国imaginist话题#理想国人文精选10部电影《南京! 南京! 》普通人和“恶”的距离有多远? 最近理想你读过的最震撼的书是“坏人:普通人为什么会成为恶魔”。 作者詹姆斯·道斯采访了参加侵略战争的日本退伍军人。 这些人在年轻时犯了被指出的坏事,在下半场致力于反战的说教。 本书不打算逃避“恶”,但在“恶事实”中暴露“恶”本身。 战争中的谁,作为普通人和我们没有任何区别,没有战争,没有必要,“如果社会制约缺席,就会出现人类的兽性。” 普通人为什么成为恶魔本文摘“坏人:普通人为什么成为恶魔”参与侵略的江波君所讲的经验:你知道,通过公共教育,他们会告诉你忠君爱国思想这样的意识形态。 换句话说,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据说日本是天神之国 那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毫无疑问。 这个观念深深植根于我们的头脑……如果你改变立场思考,这意味着让你鄙视其他种族。 那是这样的意识形态 我们从小就叫中国人肮脏的中国人,用这种方式嘲笑他们。 我们叫俄罗斯人露西猪。 我们叫西方人长毛。 所以,这意味着当天日本人加入军队去前线,不管杀多少中国人,都感觉不到杀猫杀狗有什么区别。 就像我说的,另一个理由是没有质疑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的天皇陛下是神圣的责任和最高的荣耀。 这是我们接受的意识形态。 你知道。 你参军后,这种意识形态教育会进一步加强,清除你的人格……你打仗的时候,什么时候,上级给你下达命令的时候,你完全无法抵抗。 所以我在大学学到的人道主义观念无法战胜“忠君爱国”的意识形态,后者从小就打在我脑海里。 在我心中,没有比小学和中学的教育对人的影响更大的了。 电影《日本最长的日子》要使人成为恶魔需要政治运动,要做什么样的事件? 为了下次的讨论,先从让这个问题信服的观点开始吧。 假设人类不是天生邪恶的生物,必须辛苦让他们做什么。 这些并不重要,但实际上违背了人们对战时行动的一般假设。 如果社会制约缺席,就会出现人的兽性。 事实上,甚至不需要战争。 只需要很少的承认 需要的只有医生的长袍(在米尔克的实验中显示)或制服(如斯坦福监狱实验),我们可以毫无理由地伤害别人。 但是,我们没有必要接受什么是这样的人的阴暗观点。 西塞罗( cicero )的名言“法律在战争中沉默”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道理,表示战争中会发生什么(我们抛弃了道德规范),以及战争的内部结构:不受规则的约束。 但是国际红十字会的《战时人类报告》( people on war report )强烈表示事件并非如此。 在对世界各地的平民和战斗人员进行的问卷调查中,只有4%的回答者和回答者相信“战争允许一切”。 百分之五十九相信战争是有规范的,违反者应该事后受到处罚。 64%的受访者反复认为战斗人员有“不卷入平民”的道德责任。 电影《男人们的大和》的信念并没有因为交火而崩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陆军准将马歇尔( s. l. a. marshall )主持的研究表明(至今仍有争议性),在所有战斗行动中,平均每100人中只有15到20人使用武器。 原役军人、教授大卫·格罗斯曼中校进一步指出,不需要这个比例,期和文化都基本稳定。 他对杀人的抵抗心理非常强烈,认为“战场上的士兵往往在克服这种心理之前就被杀了”。 威廉·福克纳的讽刺小说《寓言》( a fable )讲述了耶稣基督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士兵回到人类,在军队中呼吁抵抗战争,记录了当时军队高级将军中弥漫的非常现实的焦虑感。 尽管双方的死伤人数多得无法统计,但这意味着震惊士官们的非暴力行动不断出现在前线。 世代的暴力政权理解了人不是被束缚的狼,而是只放开锁链咬人的道理。 所以,暴君和战争贩子都用心思考,计划了很久,长相厮守,努力了。 他们长期以来要做很多工作来培养和维持手下的杀手。 他们需要能克服艾伦说的“动物性的同情”。 普通人看到别人的痛苦受伤时会受到其影响。 为了电影《现代启示》,政治运动需要做什么来造就他们需要的恶魔呢? 首先,各位学者同意的是你必须把他们放在一个小组里。 从法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列本到美国神学家莱茵·霍尔德·尼布尔,许多思想家用理论阐述了大众和集体行动的危险性。 在《道德人和不道德社会》( moral manand immoral society )一书中,尼布尔尖锐地谴责“人类集团道德迟钝”。 他的力量主说:“普通人无法在自己想象中实现理想化的权力和荣耀带来的挫折感”,将使自己成为集团的工具,但集团受到“欲望”和“野心”的驱使,最终为这些人提供权力的味道。 集团认为不仅是保护壳,还可以在社会动乱中感受到安全,放任不管。 尼尔和很多人主张集体行动将使道德条约的数量最小化。 集体行动的匿名性是其第一道德风险之一 在对匿名性和侵略性的开创性研究中,菲利普·津巴德( philip zimbardo )要求一名女大学生给另一名女性明确的痛苦电击。 结果发现,戴兜帽的学生和穿着宽松外套的学生相比,电击的强度大了一倍。 津巴多从这个实验中总结出,我们“去个人化”,更容易采取不关心结果的行动,自我焦点和自我意识下降。 其他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给大部分人个人化感的东西(包括大众、夜晚、面部彩色描写、口罩、墨镜等)会提高反社会行为的出现概率。 电影《现代启示》小组的一员身份不仅促进个人化,有时也促进所谓的“个人内分化”( intra-inpiduation )。 道德自我在心理上被细分。 在“个人内分化”的状态下,你的自我不会膨胀、分散,而是融入大众的通常方面。 相反,萎缩、僵化、分断是稍微独立的单位,被分割为稍窄、互不传递信息的表现,甚至相互抵触的功能。 在“脱个体化”的状态下,自己已经没有特殊性了,但在“个人内分化”的状态下,他已经没有特殊性了。 换言之,在“脱个体化”状态下,你和自己的关系是由你的集体化身份调节的,而在“个人内分化”状态下,你和他的关系是由你的特殊社会角色调节的。 他这就成了抽象的东西 “脱个体化”促进冲动的残忍,“个人内分化”促进深思熟虑的残忍。 更准确地促进残酷的合理化,避免当事人认为残酷。 进行大屠杀的艾希曼是“个人内分化”的好例子,亚瑟·苹果鲍姆认为法国革命时期的巴黎执行官查尔斯·亨利·桑森( charles-henri sanson )是更好的例子。 桑松被认为是冷血恶魔,也有人被认为是“被困在感情和责任之间的悲剧人物”,桑松本人(苹果鲍姆可能我们也是这么认为的)和律师和医生一样是专家。 电影《艾希曼》如果社会承认有必要设置处决官,就有处决官,但如果你正好成为处决官,就有责任做分内的事。 而且,把分内的事做好不是好人的条件之一吗? 我既承担了你对别人的责任(做自己的事),也承担了你对自己的责任(超越凡庸)。 负责的行刑者要求你做与典型美德无关的事,但“我不能说用刀子刺人。 律师的行为不能称为强盗。 不能说是绑架检察官的行为,对吧? ”。 苹果鲍姆想象着桑森这样问他。 是的,好的处决者会杀人。 好医生无视疼痛。 好律师会撒谎,但我们做这些事的时候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演员来做。 所以我们不是杀人,不是无视痛苦,不是撒谎。 我们只不过是处决、治疗和提供另一种选择的理论。 所以,即使律师总是“故意错误视听”,他们也不是在撒谎。 社会认可的专业化要求律师们基于他们的专业身份,我们根据我们的各种专业身份(公民、父亲、军人等),用个人角色比较具体情况的道德代替完美人的道德。 《埃诺拉盖》的飞行员似乎认为对广岛投下炸弹没有必要感到良心不安。 其实我们不是。 用这样的方法和那样的方法,可以很容易地把我们扮演的角色变成障碍。 所以我们怎么谴责我们可靠的行刑者? 我们对他们的不舒服不是由真正的道德力量引起的,而是由个人脆弱的神经引起的。 苹果鲍姆写的刑执行者是这样说的。 “我为人民工作。 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人民”。 我以他们的名义工作,为他们的福利工作,听从他们的指示工作。 所以,每次我砍头,都等于每个市民,至少每个赞成死刑的市民都会砍头。 如果他们不能责备,我也一样。 如果我应该负责,他们也一样。 “虽然是电影《金陵十三钗》,但不同社会角色的存在不足以达成反社会行为。 这样的作用对自己设置限制 法律提供最小限度的授权,人格提供最大限度的抵抗。 两个都说“适可而止”。 要制造战争罪犯,制造恶魔和恶灵,就像采访过的日本退伍军人叙述自己一样,需要相反的组合。 最大限度的授权和最小限度的人格。 你必须侵蚀为你执行杀戮命令的人的自我承认,无论是士兵还是受折磨的人,都要通过系统化羞辱他们,撕裂他们所有正常家族的身份。 把他们的自我意识集团化:让他们处理平头,穿一模一样的制服,强迫他们一起吃饭,睡觉,做操。 把他们和家人朋友和日常世界隔离开来 把他们置于系统化的生理压力和睡眠丧失之下,置于包括严厉和武断的惩罚和有时的奖项的支配系统之下。 我采访的大部分退伍军人都指出同事压力很大的影响,被欺负和屈辱,特别是挨打和巴掌。 他们也强调了上级乐于给他们的行动带来一切结果的重要性。 另外,为了制造恶魔,当权者必须利用人类服从和分组的冲动。 同样的本能也可以用于促进集体利他主义和集体道德,引导暴力。 一名英国士兵解释了这个过程:“寻找年轻人,寻找想在成年世界确立身份的年轻人,让他们相信军事力量是男性气质的榜样,告诉他们绝对服从上级的命令,相信自己属于精英群体,夸大的自我价值感。 “虽然是电影《希望与反抗》,但制造恶魔不仅需要训练,还需要故事。 在不知忏悔的战争罪犯中,你通常看到他们为了保持自我感而不现实的自我同情,做这些事让我很痛苦。 罗伯特·j·利夫顿给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纳粹医生看了这个故事的模板。 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认为这是为“不朽日耳曼民族”自我牺牲所必需的“严峻考验”。 无论在德国还是其他地方,这种自我绝对化都可以通过魅力领袖提出的历史使命和乌托邦的愿景来实现。 是通向抽象时间,甚至神话时间的心理入口,模糊了行动的个性。 所以,考虑暴力和社会作用的最好方法如下。 问题不是将其人性化为允许行使暴力的特定角色,这些作用还没有具体确定。 在战争中,一切都很奇怪 地形是陌生的,看起来不真实。 我们从小时候就依赖道德评价的参照小组中分离出来了。 没有什么熟悉的,没有真实感检查( reality check ),所以不要想得太多。 战争使我们迷惑了 然后在这个迷茫中,我们开始创造新的道德现实。 退役军人奥布莱恩( Timo’brien )写道。 “至少对普通士兵来说,战争给人灵魂般的质感,就像阴霾一样,浓厚永远不会消失。 没有什么明确的东西 一切都在旋转 旧规则不再有用,旧真理不再真实 “对”是“错”,“秩序”是“混乱”,“爱”是“仇恨”,“丑”是“美”,“法律”流入了“无政府状态”。 这雾会吸引你 你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为什么在这里,唯一清楚的只有铺天盖地的薄雾。 “纪录片《第二次世界大战启示》在《阿希从众实验》中,要求被实验者比较一些简单的直线长度。 最初,各被实验者很难正确辨别眼前的直线长度,但志愿者们被化装成被实验者的演员们包围,演员们选择了错误的长度后,其他被实验者开始关注他们,明显说相同长度的直线是不同的长度。 他们最初也表现出抵抗、迷惑和不舒服,但经过几次后,遵从小组的意见,明显露出沮丧的神色。 从这些实验中,心理学家区分了两个性质不同的“从众”,是“认识性从众”(被实验者怀疑自己的评价力)和“规范性从众”(被实验者知道集体意见不对,但不想因提出反对意见而看起来异常)。 但是,在任何情况下,这些实验都表明人容易否定自己的基本信念。 这个可怜的真理是20世纪极权主义对社会的巨大启示 基于艾伦的研究,一位学者写道。 “也许我们想不顾一切地相信。 人有什么不可动摇的东西。 关于人本身深处的东西,良知和责任感的声音不能消失。 但是,自从有了极权主义,我们就不能实行这样的信念了。 这是至今仍围绕着我们的幽灵 但更可怕的是,极权主义可能不是残忍暴行的必要条件。 如果把一群训练到坏处的年轻人放在陌生和可怕的环境中,对他们赋予不明确的作用,或者完全不约束,那么在迷茫中犯下的轻微伤害行为一定能让下一个行为看起来更正常。 给他们时间,他们最终一定会脱离原来的道德认可。 但这不是因为他们是英哈曼 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正是因为他们是人类。 点击【相关书籍】照片,可以购买源于作者詹姆斯·道斯采访二战退伍军人“中国归还者”的书。 他们年轻时犯了最残忍的罪行,但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了反战主义的说教。 作者用小说家的笔法演绎他们战时的回忆,结合本书各主题之间的脉络,收集哲学、文学、宗教和社会心理学等多门学科关于“恶”的思考,找回“邪恶”的真相、成因、背景,以及它的隐藏意义。 作者也利用此探讨了创伤带来的一系列难题和悖论,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应对邪恶和残忍等人性黑暗的一面,并探讨了在这个过程中“共鸣”能发挥多大的效果。 这种困难的人性挖掘,在读毕本书后得到解答。 喜欢这个复印件的人,也喜欢“普通人为什么会变成恶魔|“人不是被束缚的狼,放开锁链就会咬人”的原标题”原文
标题:热门:“人并不是被拴住的狼,放开锁链便会咬人”
地址:http://www.cfcp-wto.org/cfzx/1764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