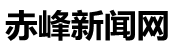本篇文章5459字,读完约14分钟
约翰·米尔斯海默活字文化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月14日宣布,美国将暂停世卫组织(世卫组织)的资助,正式开始关于世卫组织疫情对策的调查。 这一行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巨大反响 15日,CNN发表评论复印件,接连发出12个质疑美国政府在疫情预防控制方面采取的措施的问题,认为“特朗普政府有必要仔细调查对这场疫情危机的反应”。 世界知名医学刊物《柳叶刀》杂志主编理查德·霍顿说,美国政府暂停向世卫组织提供资金的决策是“对全人类的犯罪”,对科学家、医疗工作者和所有普通人,对这种对全球团结的背叛行为 自从新冠肺炎病毒袭击美国以来,特朗普政府经常发表惊人的言论。 扔锅的世卫组织主张对新冠引起的肺炎疫情有“不恰当的解决”和“隐瞒”,说“他们的错误造成了这么多死亡”,现在宣传说“非洲人在中国受到歧视”,中国的“可耻仇人”是中国的非洲 现在应该是全人类合作、共同克服困难的时期,特朗普政府的言行暴露了赤裸裸的种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 今天,活字君在与书友们共享美国国际关系的著名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悲剧”一章中表示,“大国几乎都是按照现实主义行动的,但大多主张是被更高的道德目标而不是平均的想法所驱动的。 而且,他们把对方描绘成邪恶或不道德的代替。 这样的行为模式在美国表现得特别明显 在世界舞台上,美国经常举止粗鲁,但总是异口同声地说自己的行为是道德正确的,对方的行为是邪恶的,是错误的。 “摘自约翰·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悲剧》约翰·米尔斯海默、芝加哥大学的《温德·哈里森贡献》政治学教授、国际安全政策项目主任、美国国际关系著名学者之一《纽约时报》、《新共和》、《大西洋》 《大国政治悲剧》一书的中心思想是,国际体系是危险残忍的格斗场,要想在其中生存,国家别无选择,必须为了权力互相竞争。 即使是对和平生活满意的国家也被指责参与无情的权力竞争。 这种安全竞争的根源是一个国家在受到另一个国家的威胁时没有更高的权威来寻求帮助。 国际系统中没有守夜者 而且,国家永远不能确信其他国家对他们没有敌意。 因此,他们必须为应付来自各方的危险做好准备。 我的邻居是我的朋友吗? 今天的朋友会成为明天的敌人吗? 你有足够的实力打击别国的攻击吗? 在国家意图不明的世界里,大国需要得到尽可能多的权力保护自己,免受任何国家的挑衅。 理想的结果是成为系统的霸权国家。 因为拥有这样相对权力的国家几乎可以保证其生存。 相反,软弱只会招致麻烦。 因为强国经常占弱国的便宜。 中国网民应该很容易体会到,从1840年到1949年,中国软弱四分五裂,被世界列强欺负。 《大国政治悲剧》于2001年10月在美国出版后,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和情报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在冷战后理论界的“历史终结结论”、“战争陈腐论”、“民主和平论”的呼声中,作者指出在没有国际权威支配他国的世界中,大国都是自私的、追求权力、成为支配性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大国之间必然会发生冲突 但是,没有国家能获得世界强国。 第一个理由是,很难跨越大西洋和太平洋这样广阔的水域投入力量。 即使是像今天这样富裕的美国,也不能统治世界。 但是国家可以像美国在西半球所做的那样获得地区强国。 这样,任何大国的最终目的都是控制其所在地区,防止大国在世界其他地区成为霸权国。 因此,美国全力阻止德意志帝国、纳粹德国和苏联控制欧洲,阻止日本控制亚洲。 事实上,美国在打击所有这四个雄心勃勃的对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我称之为“攻击性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给未来中美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特别是,如果中国在未来几十年内依然保持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就有可能建立美国统治亚洲的巨大军事力量,就像美国统治西半球一样。 当然,美国将努力阻止中国获得地区强国。 因为美国不能容忍有与世界舞台匹敌的同行竞争对手。 其结果是中美之间激烈危险的安全竞争,类似于冷战中的美苏那样的对抗。 最后,尽管大国几乎总是现实主义地行动,我经常主张是被更高的道德目标所驱动,而不是被平均的想法所驱动。 而且,他们把对方描绘成邪恶或不道德的代替。 这样的行为模式在美国表现得特别明显 在世界舞台上,美国经常举止粗鲁,但总是异口同声地说自己的行为是道德正确的,对方的行为是邪恶的,是错误的。 这大体上引起了很多中国网民的共鸣。 他们经常用理想主义用语谈论外交政策,但他们一定观察到他们以现实主义的方式行动。 当地时间4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新型冠状病毒大爆发简报会上指示美国政府暂停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资助。 “世卫组织没有致力于解决新型冠状病毒大爆发,疫情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大爆发。 “要创造世界秩序,大国可以超越现实主义的逻辑,集体建立培育和平与正义的国际秩序。 世界和平似乎只能增进一国的繁荣和安全 20世纪,美国政治领导人对这个论点开出了大量的空头支票。 例如,1993年9月,克林顿总统在联合国发表了演说。 “48年前,这个组织诞生的时候……许多国家有才能的一代领导人为了安全和繁荣,坚决聚集世界的力量……现在,历史给了我们更大的机会……下定决心扩大梦想吧……告诉我们吧。 尽管如此,大国不会合作促进世界秩序。 相反,每个国家都以最大限度地占有世界权力为目标,很可能与创造和维持稳定的国际秩序的目标相矛盾。 这不是说大国不想阻止战争维持和平。 相反,他们会竭尽全力阻止可能牺牲自己的战争。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行为不是由义务创造独立于一国自身利益的世界秩序,而是由狭隘地关心相对权力的动机第一推进的。 例如,冷战期间,美国消耗大量资源阻止苏联在欧洲发动战争不是因为改善世界和平的深刻承诺,而是因为美国领导人担心苏联式胜利会带来平均危险的变化。 美苏霸权随时都是某种国际秩序的出现,原则上是系统中大国自私行为的副产品。 换句话说,系统的结构是大国安全竞争的无意识结果,不是一国采取集体行动建立和平的结局。 欧洲冷战秩序的建立证明了这一点 苏联和美国都没有意图确立它,也没有共同创造它。 事实上,在冷战初期,所有超级大国都以牺牲对方为代价获得权力,阻止对方这样做。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出现的系统是超级大国之间激烈安全竞争的偶然结果。 随着1990年冷战的结束,超级大国的激烈对抗消失了,但俄罗斯和美国没有在欧洲协助建立现在的秩序。 例如,美国拒绝俄罗斯提出的各种建议,以确立欧洲安全的核心支柱,即“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取代美国主导的“北约组织”。 另外,俄罗斯强烈反对北约东扩,认为这是对俄罗斯安全的严重威胁。 但是美国深知俄罗斯的虚弱,不能进行任何报复。 这是因为不顾俄罗斯的担忧,继续推进北约东扩,接纳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波兰为该组织的成员。 俄罗斯也反对美国过去十年在巴尔干半岛的政策,特别是1999年北约对南联盟的战争。 美国再次无视俄罗斯的担心,采取必要的步骤在那个不稳定的地区缔造和平。 最后,值得观察的是,俄罗斯坚决反对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但如果美国感到技术成熟,很可能引进这个系统。 从1999年3月开始,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以“科索沃人权危机的处理”为理由没有得到安理会的授权,开始比较南联盟的空袭。 确实像冷战时一样,大国的对抗有时会产生稳定的国际秩序。 但是大国会继续寻找机会,增加其份额的世界权力,如果出现有利的形势,它们会站起来打破其稳定的秩序。 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极大地削弱了苏联,推翻了冷战后期欧洲出现的稳定秩序。 当然,权力丧失已决定的国家抵抗侵略,维持现存的秩序。 但是,他们的动机是自私的,出于平均的逻辑考虑,不是出于对世界和平的义务。 大国不能为和平的世界秩序承担义务有两个理由 首先,国家不能就增进和平的常规规则达成协议。 确实,关于这张蓝图应该是什么状况,国际关系学者并不一致。 事实上,解释战争与和平的理论几乎和从事这个主题研究的学者一样多。 但更重要的是,决策者无法就如何创造稳定的世界秩序达成协议。 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议上,如何建立欧洲稳定问题的重要分支是乔治·克莱门特·阿u、大卫·劳埃德·威尔逊。 特别是在莱茵地区的问题上,克莱门索打算对德国提出比劳乔治和威尔逊更严格的条件。 劳乔治是主张分割德国的强硬派。 因此,《凡尔赛条约》在改善欧洲稳定问题上无效而回来也不足为奇。 巴黎和谈会议是1919年1月18日在巴黎凡尔赛宫殿召开的战后协议会议。 27个国家的代表1000人参加,其中全权代表70人参加。 俄罗斯没有被邀请,德国等战败国也被拒绝了。 经过激烈的胜负和妥协,6月28日,各战胜国终于在巴黎近郊有名的凡尔赛宫镜厅签订了《对德条约》,即《凡尔赛条约》。 《凡尔赛条约》的这些条款是帝国主义重新分割世界的真实记录。 让我们看看冷战初期美国是如何考虑争取欧洲稳定的。 20世纪50年代,它为稳定和持续的系统准备了必要的重要因素。 这些包括分裂德国、美国地面部队驻扎西欧抵抗苏联进攻、确保联邦德国不迅速发展核武器等。 但是,杜鲁门政府对分裂的德国是有可能带来和平还是有可能带来战争,意见不一致。 例如,位于国务院重要位置的乔治·凯恩和保罗·尼采认为分裂的德国是不稳定的根源,但国务卿迪恩·艾奇森( dean acheson )不同意这一点。 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总统结束了美国对欧洲的保护义务,试图向联邦德国提供核武器,使后者具有核威慑力。 这个政策一次也没有实施过,但很大程度上引起了欧洲的不稳定性,直接引起了1958—1959年和1961年的“柏林危机”。 1958年,苏联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英美法在6个月内撤出西柏林驻军,之后以苏联的让步结束。 1961年,苏联再次提出了撤退西柏林的要求。 这是苏联在东柏林筑起柏林墙而结成的,美苏关系因苏联冻结柏林的问题而缓和了。 其次,大国不能放下权力,增进国际和平。 因为他们的努力是否成功还不确定。 如果努力失败,侵略者来到家门口打911也得不到答复,所以他们会为无视平均付出巨大的代价。 冒这种风险的国家很少 因此,这种谨慎的态度要求他们必须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行事。 这些理由表明,呼吁国家抛弃狭隘的平均想法,按照国际共同体更广泛的利益行动的集体安全计划必然会死亡。 国家间的合作可能会从上述讨论中得出结论,但我的理论认为排除了大国间的任何形式的合作。 这个结论是错误的 国家可以合作,有时合作很难实现,而且总是不会持久。 两种因素制约着合作:对相对利益的担忧和对欺诈的警惕 基本上,大国处于竞争的世界。 在这里,我们至少把彼此看作潜在的敌人,所以我们想牺牲对方来获得权力。 打算合作的两个国家必须考虑如何在它们之间分配收益。 这些可能会根据绝对或相对收益的标准考虑分配问题。 在绝对收益的情况下,双方都在乎自己最大限度地占有利益,不在乎其他国家在交易中的得失。 只有在其他国家的行为影响到自己权力的最大化占有的情况下,各方才会关心对方。 另一方面,相对收益的情况下,各方不仅关心自己的个人收益,还关心自己是否比其他方面获得了更多的收益。 大国重视平均势头,因此在考虑与另一方合作时,集中考虑相对收益问题。 每个国家一定想把自己的绝对利益最大化 但是,对一个国家来说,更重要的是,不要在任何协议中损害自己,做得更好。 但是,如果国家着眼于相对利益而不是绝对利益,合作就会更加困难。 这是因为关心绝对收益的国家必须保证馅饼越大至少可以增加部分份额,关心相对收益的国家需要特别注意馅饼的分配,合作的努力会变多,变成混合。 对欺诈的担心也妨碍合作 大国经常不想参加合作协定,我担心其他人在协议中耍欺诈手段,取得很大的特征。 这种担心在军事方面特别敏感,会引起“背信弃义的特殊危险”。 因为在平均情况下,军事装备的属性会迅速变化。 这样的变化可以给国家机会,使用欺骗的方法让受害者决策性的失败。 尽管合作存在这样的障碍,现实主义世界的大国也确实有合作。 均势逻辑经常促使大国结成同盟,反对共同的敌人。 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法国和苏联是反对德国的同盟国。 国家有时会像1939年德国和苏联共同对付波兰一样集结起来对付第三国。 最近的事例是,尽管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协定阻止了美国及其欧洲联盟国家通过协定,但双方还是占领和分割了波斯尼亚。 反法西斯同盟的三大企业: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的对手和同盟国合作。 结果,如果这些交易几乎反映了权力的分配,消除了对欺诈的担心,就可以成交。 冷战期间,超级大国签订的各种军备控制协定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其基础是合作发生在以竞争为核心的世界上,在这里,国家有利用他国的强烈动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40年间,欧洲的政治状况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这个时期大国频繁合作,但这种合作并不妨碍1914年8月1日走向战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与苏联也进行了出色的合作,但德国和日本战败后不久没能阻止冷战的爆发。 最令人吃惊的是,在纳粹军队进攻红军的两年前,德国和苏联可能进行了良好的经济和军事合作。 合作的多少不能消除安全竞争的主导逻辑 只要国家系统依然处于无政府状态,就不会出现真正的和平,世界总是充满安全竞争。 卫报宣布,批评特朗普攻击世卫组织是为了掩盖疫情应对失败活字文化成果的有生命力思想的原标题。 “‘在世界舞台上,美国经常粗鲁,总是说自己是道德的,对方是邪恶的’”原文
标题:热门:“在世界舞台上,美国常常举止粗蛮,却总是称自己是道德的”
地址:http://www.cfcp-wto.org/cfzx/16772.html